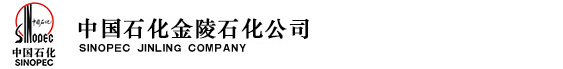作者:赵清
青野篱笆,小墙庭院。春尽夏初时,蔷薇花在浓密的绿色中重重叠叠,是夏最初的盛筵。清晨沾满露水的花枝低垂,轻触额头。微凉的风中飘落着轻柔细粉的花瓣,那里面依然有春花的娇柔纯净。
普罗旺斯或者伊犁,紫色的花海里迷迭着异域的芬芳,薰衣草在身边通常少见,也只是这两年才在江南与之相逢,那是一种聚集成海的倾心,一旦邂逅,便难以忘怀。
端午节前,端阳花就开了,一朵两朵地越开越高,农家小院的墙隅,“步步高”自然有一种朴实的喜庆寓意。它们一开数月,和紫薇花、夹竹桃一样,都是“谁道花无红百日”,一直开到秋风渐起。
市场开始丰盛起来,水蜜桃像盛放在竹篓里的花朵,这时必定有年老的妇人端着白搪瓷茶盘,像三十年前(或许还更早些),坐在市场的入口处卖白兰花。蓝色的棉布掀开,白兰花成对排列着,色如象牙,香气清雅,价钱也极为便宜。
白兰花是属于江南的母亲花。她们肤色白皙细腻,气质温柔静雅,心地善良,在花香中渐渐老去的容颜总是慈祥安静。在那样的一段岁月里,总有父亲在小院里一年又一年地养护,养护那一盆白兰花,等待花开,轻轻采撷,待一年再等花开。总有母亲一年又一年地将刚摘下的花朵包在手绢里,或是别在纽扣上,挂在胸前。一日劳作归来,洁白的花瓣已有些锈红。母亲将花朵取下,放在窗台上,夜晚有风吹过窗台,卷缩的花瓣依旧余香轻略,残存的香气却是母亲身上若有若无的气息。
这正是香花的重叠美妙时候。
茉莉花,栀子花,都洁白可喜,芬芳可喜。摘两朵青意尚存的茉莉花,拈一小撮翠绿的炒青,热水冲来,花香茶香,俱是袭人。我最喜好这新鲜的清香,深入骨髓。栀子花必成把地摘来,必和着青绿的叶,一起插在透明的玻璃瓶中,放在案头,每晚枕着花香。它们总也香着三五个日子,然后洗净容器,再换上一大把清晨初折的花枝。它原本是最俗世的花,处处可见,家家都有。然后有一句诗,一首歌将这花赋予了一些清新,那穿着淡蓝色连衣裙的少女,正走在开满白色花朵的山坡上。
可是拂落的,必是花香,不是花瓣。因为很多夏花,都是整朵坠落的,
“噗”的一声,归于大地。像那时候,我们的青春。
牵牛花,枝蔓细柔伸展,晨曦中开放,日出而合,有个非常凄楚的名字:朝颜。我下夜班偶尔回首时,瞥见它们在铁栅栏上以某种秩序摆放,蓝色的花朵从不重合,仿佛夜间散落在此间的一点点星辰。你若回眸,它便因此而灿烂起来。
地雷花,又叫喇叭花,洗澡花。它们选择在傍晚开放,在落尽日华的夜晚就一些微微的凉气。花香在暗夜的水边变得浓郁起来,任你四下里寻觅观望,也看不清它不甚美丽的花影,它愿留下的,也许,就是香气。
丝瓜花,葫芦花,瓠子花……一朵开后孕育一朵圆满,这才是花开的本意。夏花之灿烂,没有什么浪漫的含义,多半是生命初始的真谛。
夏天就铺天盖地地来了,山林街巷,树木荫荫。眼底手间,满是着绿。荷花在湖,在池塘;在满满的绿中间,亭亭地摇曳起来。隔水隔风,便听出曼妙的音乐来。它们开到残败,夏也就尽了,秋风渐起,天也就渐凉了。